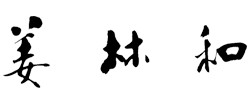再读“姜家黄山”
李绪萱
姜林和先生如果不是一位绘画奇才,怎能画出个性鲜明的水墨山水呢?艺术个性是绘画的生命。我不敢说被时间淹没了的古代画家未能画出艺术个性,因为很难看到他们传世的作品,不易做出正确判断。但我敢说,凡有作品传世的古代名家,其艺术个性都是十分鲜明的。不要说天各一方、互不影响的名家,便是同宗同派、甚至有师生关系的名家,其作品面貌也是绝对不同的。如唐代的韩滉、戴嵩,均以画牛名世,且是师生关系,面貌却不尽同。韩滉擅长“村童牧牛于风林烟草之间”,画黄牛尤能“曲尽其妙”,传世的《五牛图》将秦川牛的五种姿态描绘的淋漓尽致。戴嵩却长于水牛,尽得“野性筋骨之妙”。他俩的区别在于,老师重形,借形传神;学生重神,“得神而捷取之”。

学师而异师,方可有建树;学师而似师,必然被淘汰。当代有不少人画奔马“很象徐悲鸿”,画山水“很象李可染”,画草虫‘‘很象齐白石”,谁肯对他们刮目相看呢?谈起这类画家,顶多无不遗憾地说一句,“他们的基本功扎实”。艺术家应有扎实的基本功,但仅有扎实的基本功不能成为艺术家。姜林和先生深谙个中奥妙,所以练画时只重学习他人技法的精神,不摹拟他人的笔墨形态,更不肯花气力临摹他人的整幅作品。练则锻造自己的笔墨,画则经营自己的构图,即使面貌幼稚也不改变初衷,多年坚持下来终于跨进艺术殿堂。
我于是明白:姜先生之所以成为绘画奇才,首先在于他早早地就懂得了“画画”的本质。描摹自然形态,临模他人绘画,不是真正的画画,而是练习一种技能;真正的作画,是用自己创造的笔墨形态构筑自己对外界观察的独特感受。这个看似简单的道理,许多画人甚至于教授,一生都未明白。北京一位美院教授暮年感叹道: “我的老师太伟大了。我穷毕生精力也不能把他的东西全部学到手,创新从何谈起昵?”他对老师的虔诚令人感动,但他的绘画却不因虔诚而生色三分。姜先生彻悟得早,为他的成功埋下了伏笔。
从事绘画并取得成就,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。但不同人的成熟过程长短有别。我之所以称姜先生为绘画奇才,还在于他学画用时不太多、成熟过程相对短。他学画全靠自悟,并在有限的时间内进行,比起那些幼年拜师傅涂鸦、少年进附中苦练、青年到美院深造、成年在画院任职的专业画家来,习画的时间或许不及他们的十分之一。由于出身欠红、学途不顺、心情压抑,他从小不能不为生计奔波。后来参加了工作,先做八年苦工,再当八年厂长,继而从政八年,紧快而繁重的任务几乎耗尽了他的所有精力。因他酷爱绘画,不肯轻易放弃,所以每天夜幕深沉之后,坚持在纸山墨海中畅游几个小时。这是名副其实的业余学画,而且是在完成重业之余再去作画,艰辛不言而喻。他若仅仅视画画为“玩儿”,恐怕早就揖别了。贵在他开始便立下心愿:一定要画出属于自己的山水来。正是这种使命感,不但逼他坚持不懈地习画,而且帮他果断地排除了似锦”政治前途”的诱惑,适时地成为主业画家。他1994年出版第一本画集,时隔五年,出版了第二本画集,时年五十七岁。作品均为业余的“心花怒放”。第一本画集己显示出他惊人的造型能力,水墨山水初具了独特的神态形貌。第二本画集毫不含糊地向世人宣告:他的艺术风格已经基本定型。所绘山水,无论笔墨形态,还是构图立意,都跟他人有别,且具特殊美感。这是了不起的成就。许许多多别的画家一生都难达到的境界,他在专心画画之前、年龄不到“花甲”之时的业余时间里达到了,不是绘画奇才又是什么?姜先生善画水墨山水,尤擅黄山景观。他出版第二本画集时,我应邀作序,题日: 《妙绘黄山魂》,重点分析了他的水墨黄山的艺术特征。序文公开发表后,我接到来自长江南北的若干电话,听到了许多赞美之词。有人还说我真正写出了黄山之魂。其实,我写那篇序言之前,根本没有上过黄山。我对黄山的灵感,主要来自林和的水墨黄山。所以,若说我写出了黄山的灵魂,是由于林和画出了黄山的灵魂,并且通过画面深深地触动了我的神经。至今还有人在谈论那篇序言,那么,究竟是哪些论断给人留下了嚼头呢?

首先,我在序文的开头向人们熟知的黄山特定提出了疑问: “安徽黄山,仿佛是部深奥的书,非但千万普通游客不易读懂,就连学者、画家也难看透。无论是民间传说,还是书、志记载,对黄山的描述似乎都较肤浅。人说黄山有‘三奇’,奇在山瘦、松翠与云厚。我不敢说这种概括已接近黄山之质,但很多人相信其论为真,不少水墨画家着意表现的,也正是黄山的奇石、奇松与奇云。”
通过比较三位知名画家的笔下黄山,强调欲画好黄山确实艰难: “画黄山而无名者姑且不论,以‘黄山图’闻名于世的当代画家,耳熟能详的便有刘海粟、董寿平、郭传璋三先生。刘老情寄黄山云霞,十登绝顶精心观察,终于悟得一个‘厚’字,旋即泼以浓墨重彩,染出雄浑的刘家‘黄山’;郭老魂系黄山烟云,理出一个‘轻’字,尔后伏案细描淡写,极尽烟云婀娜多姿之态,形成清秀的郭家‘黄山’;董老独钟黄山松石,从中读出一个‘苍’ 字,从而竭力表现石之瘦崤、松之挺拔,终得苍劲的董家‘黄山’。这三家虽然各有所长,自成面貌,有着不小的艺术成就,但在许多观者眼中,他们未能触及黄山之魂,因为看了他们的作品不能联想黄山而砰然心动。”
于是水到渠成地提出问题并隆重推出姜林和先生: “那么,美术家真的不想描绘黄山魂么?未必,姜林和先生就是一位矢志攫取黄山魂的人。”
姜先生不但捕捉到了黄山之魂,而且通过笔墨将它表现出来。我在那篇序言中这样概括他的水墨黄山: “林和的黄山壮景,无论以山为主,还是云居主位,都不忘巧妙处理雄云、峻山、翠松三者的亲密关系。云团或大或小,皆成翻腾奔泻之势,但它有别于无情冲击礁山的汹涌海涛,而似胸怀博大的伟男,不知疲倦地用激情拥抱群峰、滋润翠松;山峰或多或少,都取苍润摇曳之态,丝毫没有刺天割云的华山那般脆硬,犹如坚毅而有韧劲的女中豪杰,在莽莽云海中从容周旋,顾盼生姿;老松虽绿,却不稚嫩,或探‘龙身’于峭壁,或耸‘铁柱’于山巅,不管斜出直立,均在昂头舒臂,令人想起戏云的海燕、弄潮的顽童。柔而雄浑的云团,苍而俊秀的群峰,坚而活泼的翠松,从形态到位置,在林和营造的画幅上极尽变化之能事,那磅礴的气质、抒情的笔触和清新的意境,给观众带来多层面的美感。画面上偶然出现的珠濂飞泻、琼楼半掩,则使黄山更添几丝玉宇色彩。看了姜先生的黄山图,方知不登黄山真遗憾。”
曾有先贤说过:艺术在于发现和创造。我的理解是:发现不等于看见,独家所见方能被称之为发现。黄山有名,上去的人多,大都看到了山石的千姿百态,云海的汹涌浑雄,植株的青翠欲滴。抛弃具体形态不论,但说山之多变、云之汹涌、树之青翠,难道在庐山或别的高山上就找不到么? 一般游客看到那些,并为之惊喜欢叫,无可厚非,而一个艺术家上山之后也停留在对那些现象的表面观察上,很难说他有所发现。比如说,黄山之魂就不能是表露的奇石、翠松与厚云之和,而是这三者相互影响的内在关系的闪光,不深入持久的调查研究,断然不能发现它的踪迹。姜先生发现了它。我在那篇序言中交待了他的发现:林和“在黄山南麓生活了大半个世纪,除了经常陪同各地名家上山观光之外,独自进山体验的次数己无法统计。他餐风饮露,卧石沐云,眼观云拥山摇,耳听树咏泉鸣,动情地与黄山景物交流。重点观察对象无外乎山、石、松、云,但透过它们的形体,他看到了厚重云雾吞吐八荒的奔腾气势、苍莽山石迎风起舞的雄俊身影、挺拔劲松一尘不染的青翠欲滴。它们同处一隅,相濡以沫,形成一个无时不在拥抱呼应的有机群体。三者去其一,不成为黄山;齐而无动势,并不是黄山;动而枯且燥,依然非黄山。厚云、峭石、翠松,东呼西应;拥抱、共舞、奔腾,此起彼伏;老而绿、苍而润、厚而灵,尽显朝气——这才是黄山。欲画黄山,不描绘云、山、松的互相依存不行,不表现它们的和谐动势不行,不展示它们的蓬勃生气也不行。”
纵观古今名家之作,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:他们的作品之所以不朽,一半功劳应该属于各人对客观物体内在大美的惊人发现。姜先生发现了黄山重要成员之间互动关系的韵律,便使姜家黄山成功了一半。那么,他成功的另一半是什么?
这涉及到艺术形式与深刻内容的协调统一。姜先生发现了黄山的生动深刻性,但要描绘出来,决不是垂手可得之事。那些古代名家创造、当前仍普遍使用的笔墨形态,如经典的披麻皴、斧劈皴、鬼脸皴、泥中拔钉皴、屋漏痕等等,是难以表现林和的发现的。不少画家用现成的皴法画肤浅的黄山,其面貌、意境与所画他山无异。有人将迎客松画的逼真,固然可以交待出黄山背景,但这种贴标签式的画法,又有多少艺术细胞?还有构图。如果按照传统山水技法挪移山头、布云点苔,所画出来的黄山,恐怕他只能从题目中识别了。姜先生不干这种蠢事,为铸黄山魂,他创造出一套自己的笔墨形态和构图模式。 黄山山体的主要成分是花岗岩。地壳变动时自然力作用下的撕裂、崩塌,造就出坚硬、锋利、瘦削、眷薄、多变的奇峰怪隙。稍微整体的巨峰,也被震裂成方石垒叠,上面的裂纹刚劲直延,横竖交错。虽然有些峰巅因长年风削、雨凿、水冲,失去了尖锐的棱角,凸现出浑圆的质感,却丝毫无损黄山群峰的蓬勃朝气。很多薄峰成丛生放射状,似屏风罗列,如利剑指天,仿佛是宇宙新产的艺术杰作。这种山石结构及其纹理、质感,完全不同于石灰岩质、风化严重的崇山峻岭,更大异于土石混杂的糟糠高坡。任何经典皴法的诞生,都跟一代大师为表现具体特殊对象有关。林和面对亦欲表现自己感悟到的黄山,首先想到要用新的皴法。
他惯用改良解索皴。解索皴古已有之,用法却不尽同。林和所用,实际上只是古代解索皴的大致形态,自己揉进了许多变化,因而我将其称之为改良解索皴。他的解索皴以长毫中峰写出,横直借有,以直为主;浓淡齐具,浓居多数。直非笔直,常带倾斜;横不平放,顺势高低。与古代解索皴的最大区别是:笔连不碎,线长弯少,墨浓劲足,因而力度大增,用其勾勒山形石理,峰峦筋骨立观。然后反复皴擦,积墨为阴,敷彩成阳,不但强化了有机峰峦的立体感,而且显示出黄山特有的精气神。
林和画山用笔之精巧细致,可以说到了不厌其烦的程度。为了表现黄山质感的丰富性,他在大用解索皴的同时,还参以散峰披麻皴和游丝袅空皴。后者是解索皴的变种,元代王蒙首创。林和更把王蒙的游丝细化,使其增加袅空的态势。然而,林和画云却避开了细微,所用笔触粗放阔大,常常只在山外的空白处帅气地刷上几笔水大的淡墨,任其散开晕染,居然能够形成种种魔幻一般的云天雾海。每每看到这类精彩之处,我不得不佩服他驾驭和控制墨、水的能力。在他的企望下,水载淡墨疾驰慢跑,留下许多出人意料的花样,全都构成不同的云团。厚重者翻腾不迭,忙着孕育密集的雨点;奔泻者风驰电掣,惟恐误了丰盛的午餐;悠闲者翩翩起舞,尽情展示白绫的轻盈。更有神奇者:林和从不同方向落笔,使水运墨色对撞,欲碰还离,嘎然而止,形成态势奇美的空白,仿佛是墨色厚重的画面突然敞开了心灵的窗扉,射向观众一束祥瑞的光彩。至于画树点苔,林和讲究笔笔见峰,因而无论长、圆、整、缺,皆具雀跃之态。
笔墨形态之奇美,是构筑画面的基本零件,而要完成一幅佳作,还必须有别出心裁的构图。当代的水墨山水为何存在千画一面、万人雷同的状况呢?究其根源,除了笔墨形态的陈陈相因,便是构图的缺少变化。林和构图的特点是:在山、云(或水)的关系上,他舍弃了别人惯用的山静云动(或水动)的旧模式,采用了山云(或水)互动的新格局,因而赋予大多山峰以倾斜飞跃之姿。经营山头位置时,他不用或少用一峰高耸、数峰簇拥的主辉仆衬法,而用多峰错置、遥相呼应的群辉互衬法,以显示整体气势的磅礴雄浑。他无需完善表面上的主从关系以求得画面的完整,而用所状之物内在和谐的旋律避开了画面散乱,这无疑是高一层次的整体观。
前面主要赏析了林和的水墨黄山。他信笔涂抹他山也有味道,所作花鸟亦具清新之风。牡丹极易画俗,林和的牡丹却美而含雅,品位不低,雅俗共赏,完全不同于那些一味媚俗、浓艳无骨的花被单似的牡丹图。
姜先生的绘画才能如此多面,却从来没有上过任何美术学校。他全靠自学、自悟与自创。他的成功有其特殊的外部条件。他曾有很多机会接触一大批刘海粟、唐云、启功这样的超一流画家。他未曾拜他们为师,是以老胡开文墨厂厂长身份拜见他们的。由于他为人诚实、谦恭、服务周到却不思任何索取,感动了那些老爷子。他们视他为知己,常常兴高采烈毫无保留地作画给他看。他自幼涂鸦,悟性又高,三看两看,早把那些大画家的看家本领悟透了,掌握了。这种学习机遇,是绝大多数美校生难以碰到的。他们的老师中,固然有许多大画家,但未必肯轻易地把看家本领传授出来。较为普遍的教法是:照本宣科,讲些美术、绘画的基本原理,或拿自己的习作让他们临摹。师傅带进门,修行靠自个,学生们怨不得老师。由此可见,林和虽然未上美校,却受到了更为生动、深刻、完整的美术教育。他的水墨虽然从笔墨形态到构图立意均有新貌,却丝毫没有离开水墨画的基本原理,这同那些正道走不好、专搞野狐禅者有着本质区别。之所以如此,除了他的天分、勤劳之外,还收益于广泛、亲密接触大画家的机遇。 到此为止,我把“姜家黄山”的艺术特点及其产生的背景都讲过了,不知对读者欣赏姜氏画作有无帮助。读画与作画一样,能不能达到高境界,悟性是必不可少的。希望大家相信自己的悟性。